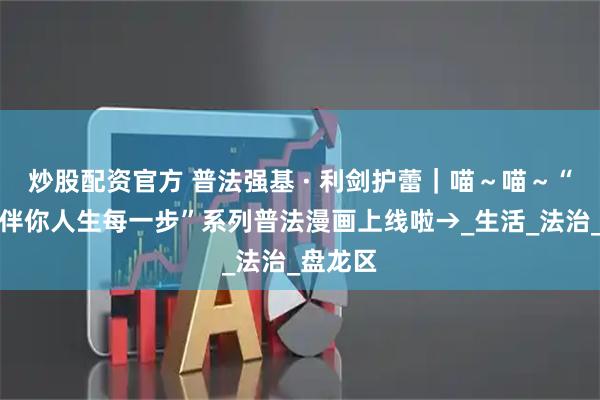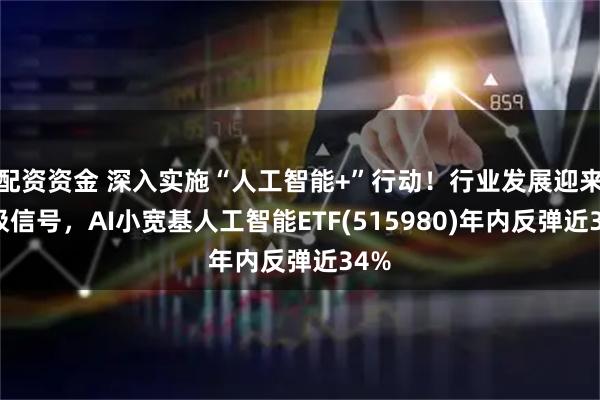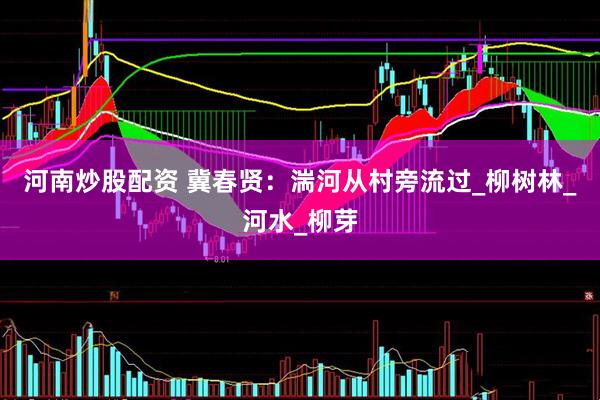
昨夜梦回故居河南炒股配资,儿时的家乡不时在脑海浮现,回味无穷,留字存忆。
在古老的中州大地,有一条不太出名的河叫湍河,它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翼望山,因河水在上游穿峡切割而下,水流湍急,故得名“湍河”。湍河如同一条白色的玉带在两岸村庄的中间地带蜿蜒曲折,时而两岸平坦,河水缓缓而流;时而两岸陡峭,河水夹紧腰身穿行而过。流经两百多公里后,它注入另一条河流 —— 白河,从此结束自己的征程。
在湍河的中段,有一片开阔的河床。河东沿岸是大片大片的柳树林,穿过柳树林有一堵高高的寨墙,寨墙围着的村庄就是我的家乡冀寨。它因村里三千多人都姓冀,也因兵荒马乱之年为保村民安全而高筑寨墙而得名。
湍河从村庄的西边流过,平缓而温柔,为家乡平添了几分姿色。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,湍河河水清澈见底,成群的鱼虾无拘无束地游弋其中,时而有快乐的小鱼跃出河面,满身的鱼鳞闪着道道银光。河的西边是一大片闪着点点金星的银色沙滩,湿润的沙滩上有无数个酒窝似的浅浅小沙窝。用手指一抠,或用脚趾一拱,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白里略带点粉色的小蛤蜊便露了出来,那是水鸟和乌龟的美食。河水中及沙滩上有野生的老鳖,它们用后腿在沙滩上刨出一个窝作为自己的 “别墅”,厚厚的沙子覆盖在背上,只露出一个麦秸杆似的鼻孔在外透气,一般人看不出来。当地人戏称:“只有长着鳖眼、懂得鳖路的人才能看到。” 河边常有懂鳖路的人下河捉鳖,他们不带任何工具,徒手擒拿。逮住猎物便脱下上衣,袖口一挽,把老鳖装进袖管。沿河走上几里地,常有七八只甚至十来只老鳖的收获,两只衣袖装得满满地,搭在脖子上满载而归。
展开剩余82%河水中常年有出双入对的鸳鸯、成群的野鸭在河水中钻进钻出,觅食戏水。夜晚,鸳鸯双宿,野鸭群居于水中或安卧于岸边柳树垂在水中的根须下安眠。
春天来临之时,河东边的柳树林中千万条柳丝犹如少女美丽的长发,随风起舞,婀娜多姿。细细的柳条上缀满小小的、尖尖的柳芽苞,没几天,冒尖的小芽苞就变成了嫩绿的柳芽。柳树林如同碧玉妆成的海洋,随风摇曳,撩拨着人们对它的喜爱。嫩绿的柳芽还为当时粮食短缺的人们提供了部分食材,常有人捋些柳芽洗净,拌点红薯面蒸了,撒上蒜汁,便是进肚的美味;也有人将柳芽蒸了晒干泡茶喝。
白天有数不清的鸟在林中飞来飞去,有几种捕鱼能手常在河面绕飞,瞅准目标急速俯冲而下捕捉鱼虾。最常见的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为“钓鱼钩” 的鸟,每次俯冲几乎 “弹无虚发”,飞起之后常有小鱼横在它们嘴中拼命挣扎。吃饱喝足之后,它们栖于林中柳枝鸣叫,好不惬意。有的鸟没有下水捕食的能力,只能在树间觅虫,最多的是黑色的老鸹,雅号乌鸦。老鸹们成群结队常年在树林上空绕树飞行,发出 “哇 —— 哇” 粗劣嘶哑的叫声。虽然当地人喜欢听叽叽喳喳的喜鹊叫,而不愿意听老鸹那被认为不吉利的叫声,但是,因为老鸹对环境的选择极其苛刻,这里清净的河水与空气,使柳树林成了它们的不二选择。老鸹们比当年的曹操强多了,曹操当年曾感叹 “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”,而这些老鸹不论飞多远,不论到哪里觅食,也不论绕树多少匝,总有无数柳枝可供栖息。白天,柳树林是鸟的天堂;夜晚,这里是它们的别墅,它们栖息于绿枝绿叶间安眠,做着人类不懂的鸟梦。
夏天之时,柳树林是人们乘凉的好去处,没有泥巴、没有任何污染的沙河是人们天然的澡堂。不论白天还是晚上,总有人在河水里洗澡、戏水、打水仗。现在想起,当年的一些画面仍历历在目,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疯狂的小脚老太,人称“喳啦子” 的三奶奶。五六十岁的她每次下河洗澡,就像带去了一台戏。她洗澡前的热身是站在河岸上,光着脊梁,穿个大裤衩,光着尖尖的小脚,张开双臂甩上几甩,两只耷拉的乳房随着摆动的胳膊上蹿下跳。然后从岸上 “扑通” 一声直扑到水中,溅起一圈浪花,紧接着是泡在水中人们的大笑声、起哄声、用手或盆往她身上的泼水声,以及她与晚辈们的嬉笑怒骂声,形成了奥运会上也绝不会出现的水上交响曲。
人们洗完澡爬上岸,借着柳树林中的树丛遮掩换上干衣服,然后在柳林中乘凉。时不时还有人在柳林里支起棋牌,肆意拼杀。小孩们用柳枝条在地上画出一个方块,再画出对角线,形成四个小三角,在其中一个小三角中画一个小圆圈,称之为“井”,摆上四颗石子,两个小朋友便开始了占方大战,直至把一方挤兑得无路可走,只能跳井,便决出胜负。
夏天的河水也有暴怒的时候,每当上游出现大面积的暴雨,湍河就要涨水。涨水时,水头会像一堵长长的高墙,齐刷刷轰然怒吼而下。水头到来前的河床中和沙滩上,会有被强大的水压挤压而冒出的无数个水泡,咕咕嘟嘟作响,好像锅滚了一般。紧接着便是六七尺高的浑浊水头排山倒海顺流而下,引起一河两岸老百姓的惊呼和呐喊,那景象一点也不比钱塘江潮逊色,只是湍河潮不出名罢了。
水头过后,暴涨的河水一改往日的温柔面目,狰狞可怕。黄黄的浑浊河面会宽出两三里,一直淹没到一河两岸的沙滩和柳树林,直逼寨墙跟下。河中央激流翻滚咆哮而下,河中常有冲下来的带着根须的树木、麦秸垛、木板、门窗、桌子、柜子、猪、羊、西瓜等杂物,那是上游人们受灾的象征。记得有一次,河水中央的激流处,冲下来一根木头,上面骑着一个男人大喊救命。可是水太大太猛,下水等于送死,没人敢下。岸上的人们心急如焚,只能大声喊话让他抱紧木头,眼睁睁看着他骑木顺流而下,也不知那人最后的命运如何。
水,是那么温柔,哺育了人类及万物;水,又是那么“无情”,变作 “洪水猛兽” 时会荡涤吞没它路过地方的所有!
秋天,柳树林开始由绿变黄,秋风吹来,柳叶纷纷落下,地上好似铺满了黄绿色的地毯。但是,这地毯不会长久,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缺少做饭的柴火,柳树林的落叶便成为当地人们烧火的补充品。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,人们就拿着扫帚、背笼或大筐,开始就地取材扫柳叶。去得早的人们,会先在柳叶较厚的地方拿扫帚扫出一个大圈,圈起一个边,无声地告诉人们圈内已被占据,这是我的。去得晚的人,只能圈个小圈;再晚去的人,只能去扫边边角角的地方。所以,柳林中每天落下的柳叶几乎每天都被清扫干净,直至柳林无叶可落。
每年的冬天,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成群大雁,在空中一边飞行,一边发出“咯嘎、咯嘎” 的鸣叫,队形一会儿变成个 “一” 字,一会儿变成个 “人” 字,和小学语文课本上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小孩们常仰望天空,伸长脖子,伸着一根手指数着空中雁群的数量,但数来数去总也数不清。夜晚,雁群栖息在河西边大片银色的沙滩上。风高月黑之夜,常有村中的年轻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涉水而过,然后躺倒在沙滩上去滚雁。滚到雁群栖息处抱走几只大雁,雁群才知那滚动的黑物不是同类,继而引来一片惊鸿鸣叫和呼呼啦啦的起飞声,真个是 “月黑雁飞高”。
我和邻家的几个女孩,也常在冬日较暖的天气,卷起棉裤腿,趟过冰冷的河水,赤着冻红的双脚到对岸沙滩上捡雁翎。拿回家后,剪下雁翎下的空管,一劈为三做脚,缝在用铜钱做成的底座上,然后去物色尾巴周围长有漂亮鸡毛的公鸡,拼命追赶,鸡飞鸭叫,直到逮住为止。可怜的公鸡被牢牢地抱在怀里,随着它一声声惨叫,尾巴上红里带点黑、油光发亮的鸡毛被一根根拔下,直到雁翎管内被鸡毛密密匝匝地插满方才罢休。每一个漂亮鸡毛毽子的诞生,往往有一到三只公鸡遭此大难,现在想来实在对不起那些公鸡们。此时,我那个漂亮的鸡毛毽子之王仿佛就在眼前:鲜绿色的布缝出的底座,大红线撩着花边,粗粗的白色雁翎上插满闪亮的鸡毛,鸡毛以雁翎管上口为中心向周围均匀发散,呈弧形向下耷拉一圈,那样子实在好看。那时的我,利用毽子之王一口气能踢出八十多个,用脚后踢,能弹蹦踢出十四五个。那时的我,一晃成了现在的老太,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!
从寨墙下上斜坡到寨墙上,往里走大约 50 米的地方,有我的家,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和一座古朴的龙门。站在龙门口可以看到河里的景象,按现在的标准也算是一座 “河景房” 了。在这座 “河景房” 里,送走了我的祖奶、爷爷、奶奶和我的父亲,养大了我们姐弟五人。现在,家人们早已另迁新居,“河景房” 的龙门及堂屋的门不知何时被贼偷走,东西两边的房屋成了断垣残壁,废墟上长满了邻家种植的各种蔬菜,青翠欲滴。
村子北边有提灌站,抽水机突突地把河水抽上高坡的机房,再从机器的水管中流出。刚出水管口的河水翻冒着白色泡沫形成一团浪花,而后像一条温顺的玉龙流入渠沟,灌溉着村子东边的千百亩良田。田里有水稻、藕池,稻田藕池中有鱼游,有水鸟,有蛙鸣,还有吸人血的蚂蝗…… 记得当年有同学在作文中描写我们的村庄是:“东坡飘来鱼米香,西边柳树栽成行,北坡传来马达响,南坡烟叶三尺长。”
这就是我儿时的家乡,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:河水、沙滩、柳林、村庄、寨墙、草房、纺花车、织布机、打麦场、牛拉车、水打磨、驴拉磨、人推碾、炕烟楼、烧砖窑、渠沟、良田…… 古朴无华、美丽自然,人们虽不富裕但精神满足,忙碌并快乐着。
作者:冀春贤,女,生于五十年代,河南邓州人,经济学教授,现退休。
声明:此文转载自网络河南炒股配资,旨在展现邓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魅力。谨此向作者致敬!
发布于:河南省旺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